无论是转换心情、做出决策还是采取行动,你头顶的那个大脑,都不是你身上唯一一个进行思考的部件。
这是一个很不顺心的早晨。你上班迟到了,错过了一个关键的会议,现在你的老板对你十分生气。所以你在午餐时直接走过沙拉区,直奔那些特别油腻的食物。你控制不住自己——在我们倍感压力时,大脑会鼓励我们寻找“慰藉食物”。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或许并不是那个藏在你颅骨里的大脑,而是你的“另一个大脑”。
是的,你没看错,你还有“另一个大脑”。你的身体里还有另一套独立的神经系统。其机制实在太过复杂,因此常被人戏称为“第二个大脑”。它拥有大约5亿个神经元——差不过是大鼠大脑神经元的5倍之多;它大约有9米长,从你的食道一直延伸到你的肛门。或许正是这个大脑,让你在承受压力时更加渴望薯片、巧克力和饼干。
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嵌在肠道壁上。科学家从很久以前就知道它能控制消化运动。但现在看来,它似乎也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既可以独立工作,也可以跟你头顶的那个大脑通力合作。虽然你意识不到自己的肠道正在进行“思考”,但是肠神经系统确实可以帮助你察觉环境中的威胁,进而影响你作何反应。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的迈克尔·葛森(Michael Gershon)介绍说:“肠道向大脑发送的大量信息,都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甚至都意识不到。”
如果你“潜入”人体内部,你肯定能找到大脑,还有那些从脊髓发出来的末梢神经细胞。但肠神经系统是一套广泛分布在两层肠道组织里的神经网络,远不如大脑那样明显(如下图)。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家才发现了它的存在。它是自主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自主神经系统属于外周神经系统,专门负责控制内脏的运作。它也是“原始的神经系统”(original nervous system),早在距今5亿年前的首批脊椎动物身上就已经出现。后来随着脊椎动物不断演化,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有可能是它促进了大脑的形成。
消化当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所以有一套专门的神经网络负责调控,确实合情合理。肠神经系统不仅可以控制食物在胃中的机械混合、调节肌肉收缩从而让食物在肠道中移动,而且还能维持肠道不同部位的生化环境,维持消化酶工作所需的正常酸碱度和化学组成。
但是肠神经系统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神经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吃东西总会带来危险。因此肠道跟皮肤差不多,它们都必须阻止潜在的危险入侵者——比如细菌和病毒——进入身体内部。如果有病原体穿过肠壁,肠壁上的免疫细胞就会分泌包括组胺在内的发炎物质(inflammatory substances),让肠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捕捉到危险信号。然后“肠中大脑”要么会催发腹泻,要么会警告“头顶大脑”。而“头顶大脑”可能会决定催发呕吐反应,或者让人上吐下泻。
你一定知道这些激烈的肠道反应,或者某些轻微一点的,伴随兴奋、恐惧和压力而来的胃部感觉——你甚至都不需要成为一名肠道病专家。过去数百年来,人们一直相信肠道会与大脑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人类健康,或者给人带来疾病。不过直到上个世纪,科学家才开始仔细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联。该领域的先驱人物有二:一位是美国医生拜伦·罗宾逊(Byron Robinson),他在1907年出版了《腹部和盆骨中的大脑》(The Abdominal and Pelvic Brain);另一位是跟他同时代的英国生理学家约翰内斯·兰利(Johannis Langley),他发明了“肠神经系统”这个词。大约就在那个时候,科学家才清楚了解到肠神经系统可以自主运作;就算把它和大脑的主要连接——迷走神经——切断,肠神经系统依然能调控消化运动。虽然科学家做出了这些重大发现,但是学界对“肠中大脑”的兴趣曾经一度衰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为“神经胃肠病学”(neurogastroenterology)的新领域才横空出世。
我们现在知道,肠神经系统不仅可以自主运作,而且还能影响大脑。事实上,在迷走神经传递的信号中,大约90%都并非来自“头顶大脑”,而是来自肠神经系统。
是什么让你感觉良好?
我们的“第二个大脑”跟“第一个大脑”有许多共同特性。比如它也是由多种不同类型的神经元组成的,而且也拥有胶质支持细胞。它也有自己的血-脑屏障,可以让自己的生理环境维持稳定。它也能产生种类纷繁的激素和大约40种神经递质,与大脑中发现的神经递质属于同一类型。事实上,科学家认为肠道神经元产生的多巴胺,就跟“头顶大脑”产生的一样多。最有意思的是,无论你何时进行测量,人体内大约95%的血清素都存在于肠神经系统之中。
那么这些神经递质到底在肠道中做了什么呢?大脑中的多巴胺,是一种与愉悦和奖励系统有关的信号传导分子。肠道中的多巴胺也同样是一种信号传导分子。比如它可以在神经元之间传送消息,协调结肠肌肉收缩。肠神经系统里的另外一种信号传导分子是血清素——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感觉良好分子”,因为它可以防止抑郁,还能调节睡眠、食欲和体温。但是它的影响远不止如此而已。肠道产生的血清素可以进入血液之中,参与修复肝脏和肺部的受损细胞。它对于心脏的正常发育也十分重要,还能通过抑制骨骼形成来调节骨骼密度。
但这又会对我们的心情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的“肠中大脑”本身显然没有情感,但它是否会影响“头顶大脑”产生的情感?科学家一般认为,在肠道中产生的神经递质不能进入大脑——虽然从理论上说,它们可以进入缺乏血-脑屏障的小型大脑区域,比如下丘脑。但不管怎么说,肠道向大脑传送的神经信号,似乎确实可以影响心情。比如一项发表于2006年的研究指出,在其他治疗手段都失败的情况下,刺激迷走神经也可以成为一种治疗慢性抑郁症的有效办法。
我们似乎也能通过这些由肠道传递给大脑的信号,来解释为什么油腻的食物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当我们摄取食物的时候,肠道内壁的细胞受体可以感觉到脂肪酸的存在,然后向大脑发送神经信号。不过它的作用似乎不仅仅是让大脑知道你都吃了什么。研究者往一群志愿者的肠道里直接注射脂肪酸,给另一群志愿者注入生理盐水。大脑扫描结果显示,注射脂肪酸的被试对悲伤图画和音乐产生的反应,不如对照组那般强烈。他们向研究者报告的伤感程度,大约也只有对照组的一半。
另外还有证据显示,当我们对压力做出反应时,我们的两个大脑之间也有联系。有句英语俗谚说得好,“胃里仿佛有群挣扎不安的蝴蝶”。这其实说的正是大脑触发“战斗或逃跑”的反应之后,血液离开胃部、进入肌肉给你带来的感觉。压力也会刺激肠道产生更多的生长素——这种激素不单会让你感到更加饥饿,还会让你感到不那么焦虑和抑郁。生长素也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它既可以触发快感和奖励系统中的神经元,进行直接刺激;也可以通过迷走神经传递的信号,进行间接刺激。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的杰弗里·齐格曼(Jeffrey Zigman)介绍说,在我们的演化历程中,生长素在缓解压力方面可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在野外冒险搜寻食物时需要保持冷静。他的研究小组在2011年报告说,受到慢性应激刺激的小鼠会寻找脂肪含量高的食物,而因为基因改造无法在刺激下合成生长素的小鼠则不会受到影响。齐格曼指出,我们现代人可以轻易获取高脂肪含量的食物;因此慢性应激刺激或抑郁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长期提升我们的生长素水平,而且还能造成肥胖。
我们的肠道和精神状态之间,为什么会演化出如此强烈的关联性?葛森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肠道获得大量的环境信息。他说:“请记住:我们肠道内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外的世界。”所以我们不单可以通过眼睛看到危险、通过耳朵听到危险,还能通过肠道侦测危险。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Neurogastroenterology)的神经胃肠病学主任潘卡·帕斯理查(Pankaj Pasricha)指出,如果没有肠道,就没有维持生命的能量。他说:“肠道的活力和健康运作特别重要,所以大脑需要跟肠道建立起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两个大脑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区别在于“记忆”——但是葛森不这么看。他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名美国军医院的护士,在每天早上10点钟准时给病房里的瘫痪病人灌肠。在他离开医院之后,他的继任者取消了这套流程。但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病房里的所有患者都自动开始进行排便运动。虽然葛森承认,除这则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轶事之外,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肠道记忆”的报告,但是他愿意对此观点抱持开放的态度。
肠道与“直觉”
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决策了。“直觉”或“直觉反应”两个词的英文一个是“gut instinct”,一个是“gut reaction”,都包含了“gut”——也就是“肠道”。但其实“胃中有蝴蝶”之类的反应,根源仍然在于大脑传来的“战斗或逃跑”信号。这类信号会让我们产生焦虑或兴奋之感,进而影响我们的决策,让我们决定该不该玩蹦极,或者该不该安排第二次约会。但是这些决策是否有可能来自于你的“第二个大脑”?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潜意识中的“直觉”,确实需要肠神经系统参与;但真正感觉到威胁的,其实还是我们头顶上的大脑。就连葛森都认为,我们的“第二大脑”无法进行有意识、有逻辑的理性判断。用他的话说:“宗教、诗歌、哲学、政治——这些玩意全都属于‘头顶大脑’。”
不过我们也逐渐了解到,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发育成熟的肠神经系统,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远不止消化不良这么简单。帕斯理查发现,如果对新生大鼠的胃部施加较为温和的化学刺激,会让它们比其他大鼠更加郁闷和焦虑;即使在生理损伤痊愈之后,心理症状也仍然会持续很长时间。他说,包括刺激皮肤在内的其他伤害,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另外,研究者也发现,母乳中包含催产素在内的多种成分,都有助于肠道内神经元的发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未经过母乳哺育的早产儿,更容易罹患下痢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部分肠道发炎坏死。
血清素对于肠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来说也至关重要。身兼数职的血清素,在此扮演的是“生长因子”的角色。肠神经系统中负责生产血清素的细胞,很早就已经开始发育。葛森在突变的小鼠身上发现,如果该细胞的发育受到干扰,“第二个大脑”就无法正常发育。葛森认为,儿童早年经历的肠道感染或极度压力,可能也会带来同样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他们以后患上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其主要症状是慢性腹痛和频繁腹泻或便秘,而且常常伴有抑郁。因此,肠易激综合征的产生原因,有可能是肠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变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最新研究的支持。研究显示,在100个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病人中,有87人体内带有可以攻击和杀死肠道神经元的抗体。
综上所述,肠神经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前对“第二个大脑”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帕斯理查说:“它如果发生畸变,会给我们带来不少苦头,”他认为,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第二个大脑”,必将有助于我们控制各种病症,无论是肥胖、糖尿病,还是阿茲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这类通常被认为与大脑有关的疾病。然而到目前为止,意图探究“第二个大脑”的研究者仍然太少。帕斯理查说:“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但是它目前受到的关注实在太少。”
肠道与神经系统疾病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我们肠道里的神经系统绝不仅仅负责消化。部分原因在于,科学家发现“第二个大脑”与多种大脑疾病有关。以帕金森氏症为例:这是一种与运动和肌肉控制有关的疾病,其病因是大脑中负责生产多巴胺的细胞损失。但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海科·布拉克(Heiko Braak)发现,造成细胞损失的蛋白质团块“莱维小体”(Lewy bodies),同样也出现在肠道内负责生产多巴胺的神经元中。布拉克检查了死于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体内莱维小体的分布状况,认为莱维小体其实最早出现于肠道(可能是病毒等环境因素造成的),继而经由迷走神经扩散至大脑。
与之类似,在阿兹海默氏症患者大脑里找到的特征斑块或缠结,也同样存在于他们的肠道神经元里。我们知道,自闭症患者也容易患上肠胃病——科学家认为,引起这类肠胃病的,正是那些影响大脑神经元的基因突变。
潘卡·帕斯理查介绍说,虽然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两个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肠道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研究大脑病理学的窗口。“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通过肠道活检进行早期诊断,也能以此来监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
“第二个大脑”里的细胞甚至还能“还诸彼身”,用于治疗。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有一种实验性的干预方法,需要把神经干细胞移植到大脑里,以补充损失的神经元。但从大脑或脊髓中提取神经干细胞并不容易。不过科学家现在已经在成年人的肠道中找到了神经干细胞。从理论上说,这些神经干细胞可以通过简单的内窥镜肠活检手术提取出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神经干细胞来源。事实上,帕斯理查的研究小组目前正计划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包括帕金森氏症在内的疾病。
编译自:Gut instincts: The secrets of your second brain,NewScient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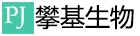 过敏菌商城
过敏菌商城
